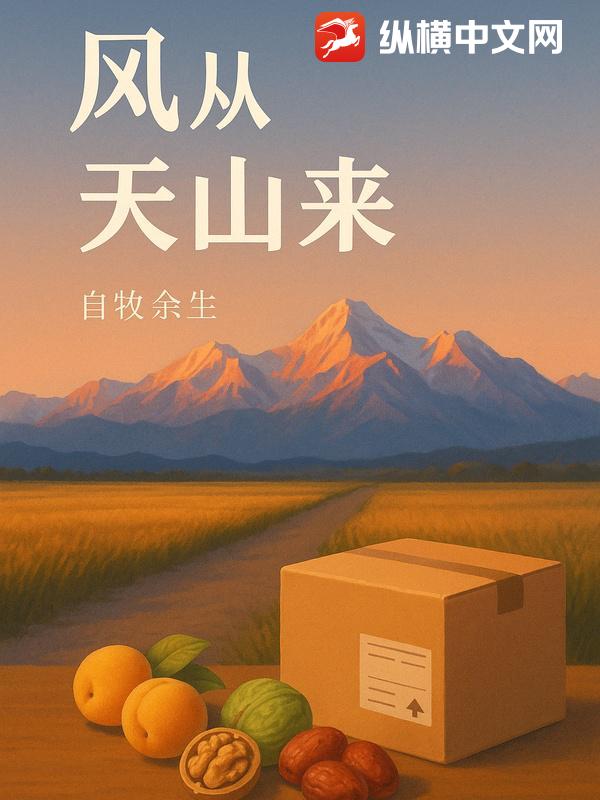巷口的风一早就起来了,带着细细的沙。吐尔逊把铁卷帘半掀着,探头看了看天色,又退回去摸冷柜的侧壁,耳朵贴过去听那一丝低低的嗡声。
他抬起脸冲院子摆了摆手:“稳着,没事。”李明点点头,把手里那本记录夹扣上,心里却还是记了一笔——这几天风大,电压不太稳,冷柜得多看两眼。
院里,苏蔓把软木板立在门口,贴上新的“今日安排”。她把卡纸边缘压实,回头问古丽:“你再看一眼,我怕漏了。”
古丽过来,把“回访”和“准备会”两个字轻轻敲了一下:“就这样,别再添东西了,够了。”两人对视一眼,都笑了笑——忙到这个时候,能把“少做一点”当作一种稳,这也是这些天学来的。
买买提江把车倒进巷口,车里还有昨晚从县里捎回的纸箱样板。他一把把纸箱往下搬,顺口说:“胡老板让带句话,城里那边这两天又有人打听你们的唛头样式,让你们当心。”
李明应了一声,把样板抱进屋里,手指摸过那道折痕,心里像在画直线——规矩摆在明处,心就不乱。
上午没安排什么“新活”。李明只挑了两件看上去不急、却非做不可的小事。
第一件,去吐尔逊店把冷柜的记录表换新,把过去一周的温度曲线抄到本子上。
吐尔逊把店门虚掩,示意他进里屋,屋里光线暗一点,冷柜两侧贴着厚厚的胶带。李明沿着胶带摸过一圈,心里头是一种老工人的谨慎——靠得住的,多半不是嘴上的好听话,而是这种一层一层贴上去的“板正”。
第二件,是把“公开查验”的流程卡再写一遍,贴到院门跟前,字写得比以前更大,远处一眼就能看清。
古丽拿过来,像平时那样,把“谁说了算”“当场说清楚”圈出来,画了两笔,挂回去。
午后,风更硬了,天边有一线发白的光,像谁把纸捋了一下。
胡老板过来时,胡须上落了些细沙,他进门先咳了一声,把壶放下:“你们下午要去巴扎不?”李明说:“不去了,今天在院里回访。”
胡老板“嗯”了一声,眼神却先落在那块软木板上。他站着看了几秒,抬手点点“准备会”三个字:“这字写得正。会开得正,心就不散。”
“你那边的摊子还稳?”李明问。
他没绕弯子,胡老板也不躲,摊开手:“稳,没拦着人,也没人再来挑衅。我这人你知道,脾气冲,可我服理。理给到这儿,我就不闹腾。”
他说着笑了一下,“倒是有人背后嘀咕,说我跟你们站一条线吃亏,我回他一句——‘心定着,别怕慢。’”他说“别怕慢”三个字时,把手在桌面上按了一下,像把什么钉住。
这会儿,马合木提提着一袋枣干进来,脸上有风刮的痕。他把袋子放下,往后退了一步:“我家屋后那几袋,你们明天有空看一下,我自己分了,可没你们分得细。”
古丽出去看了看,回来点头:“行,明天过完早上的事,我跟你过去。”
马合木提“唉”了一声,眼睛里头那点迟疑像是被什么压下去了:“那我就等你们。”他转身走了两步,又回头补一句,“我女儿把字练得差不多了,‘五米能看清’,她说要给你们写一块大的。”
李明笑着答:“让她写,我们给她上墙。”
到了傍晚,院门外来的人多起来。不是来看热闹的,都是熟面孔,提着自家的小问题,围坐在院子里把话说开。
有人问礼盒的事,阿衣丁就坐在一边,说“我这次订婚,礼盒就按他们的样式做,清爽,不花哨,长辈看着顺眼”。
有人问“丢件了怎么算”,苏蔓把流程说了一遍,末了加一句,“别憋着,有事就当场说,别等着心里堵出个疙瘩”。
有人提到“城里那摊子”,胡老板把话接过去,慢慢说:“看清楚牌子,别听两句热闹话就下手,咱自己这条路不怕人看,有啥都在明处。”
风一阵一阵把人说话声往外翻,院里却不乱。李明坐在台阶上,听大家说,也不插嘴。
等众人要散的时候,他才站起来,冲大家说:“谢了。你们愿意来,把话放在桌上,就是帮我们。以后有啥话,还是这样说。”人群中有人“嗯”了一声,又有人笑起来:“说清楚,心里踏实。”
散场时,天已擦黑。吐尔逊从店里搬出两块冰板,喊了一声:“放在门里,省得夜里跳温。”苏蔓赶过去接,笑着道谢。吐尔逊摆摆手:“都是一条街上的,谁看谁的面子啊。”他顿了下,又小声说:“晚上我再看一眼电表,风大,别出乱子。”
夜里风小了一点。李明把明天要用的纸箱样式放在桌上,手指沿着边折过去,整个屋子只有纸壳被压过的声音。古丽从外面进来,手里捏着一张油渍小纸条:“阿衣丁让的——礼盒名单。”
她把纸递给他,笑了一下,“他人很紧张,嘴上不说,手心全是汗。”李明接过纸条,念了两遍那些名字,像把一个个位置在心里排好,又折进去,夹在透明夹层里。古丽看他收纸条的手法,笑意又深了一点:“你这人喜欢把东西夹得整整齐齐。”李明“嗯”了一声,“夹稳了不丢。”
两人正说着,苏蔓接了个电话,表情有些奇怪。
挂断以后她走到门口,靠着门框叹气:“我妈让我回乌市,说有个正经工作,别在这边‘折腾’了。”
她说到“折腾”两个字的时候,用手指在空中比画了一下,又垂下去,“她意思我年纪不小了,别老飘着。”
屋里安静了一会儿,古丽先开口:“你想走吗?”苏蔓摇头,又点头:“我舍不得,但我也懂她。”
李明没有劝,只说:“你把心里话跟她说清楚。我们这里,不靠谁一个人撑着,谁走谁留,都要过日子。你要走,我们给你收拾好;你要留,你把自己站稳就行。”
这话说完,空气里那点绷紧的东西松了些。苏蔓吸了口气,笑了笑:“别急着把我送走,我还没想好。”她把手机放回兜里,“明天我先把礼盒那条拍了。”
第二天一早,风小了。李明把要带去县里的资料装进袋子。赵书记一早来院里,没坐,就站在门口说:“县里那边打了招呼,下周让你们去讲一次,不是说大道理,是把这一路怎么过来的讲给周边几个乡镇的人听。你们挑人自己商量。”
他说话的劲头跟往常一样,一句顶一根钉,钉完就转身,“我先走,你们忙。”
人一走,屋里安静了两秒。古丽看着李明:“你去?”李明笑:“我不一定讲得好,你们两个比我会说。”
苏蔓举手:“我可以把流程和坑点讲明白,少讲那些绕人的词。”古丽想了想:“我讲‘怎么跟人说话’,别讲那些框。你要不要再挑一个人?”
李明把目光从屋里转到院子,看到马合木提抱着两捆空袋正从门口走过。他喊住人:“有空吗?想不想跟我们去县里讲讲?不讲那些难的,就讲你那次被退货以后怎么做的。”
马合木提愣了一下,下意识摆手:“我不行,我说不利索。”古丽笑:“你就说你怎么挑的,怎么被拒了又怎么改的,别心虚。”马合木提挠挠头,脸有点红,过了会儿点点头:“那我试试。”
中午前后,风停了,太阳露出一角,巷口的光一块一块地移。吐尔逊从店里出来,向他们招手:“电表那边好了,换了个稳压的,小伙子刚走。”
他一指墙角那条新的电线,“这下夜里放心些。”李明竖起大拇指:“谢了。”吐尔逊摆摆手,嘴角翘了一下:“用得住,才是好。”
下午,院里练了一次“讲”。没有讲台,没有话筒,只是一把椅子、一张纸。
苏蔓先来,讲“怎么把事说在前头”。她不铺垫,开门见山:“先把丑话说在前头,大家就少一半误会。别怕丑,丑话说清楚了,脸就不丑。”她把那张“公开查验”的流程卡举起来,拍了一下,“这东西就是丑话。”
人群里笑了一声,笑过之后点头的多。
古丽接着讲,讲“谁说了算”。她举了两个小例子,一个是老人执意要多塞两把核桃,一个是远方的亲戚托关系要插队。
“谁都不想得罪人,可不把‘谁说了算’立住,最后还是得罪人。”她说得慢,眼睛看着每个人,“我们立的规矩好看吗?不好看,可它管用。”
最后是马合木提。他起身时还不太敢看人,手心有汗。可开口后,声音并不抖:“上次他们不收我的果子,我回去挑到半夜。我心里骂了一路,骂完我又想,我要是他们,我也不收。第二天我就按他们说的挑,再送来,过了。就这事,我回家跟女儿说了一遍——你字写出格子,就得擦掉再写。她听了,也没哭。”
这一段说完,人群一时安静,紧接着响起一片“行”的声音。有人笑着说:“就该这样。”
练到傍晚,院门外忽然阴了一块。风像有人忽然把窗户拉开一样灌进来,桌上几张纸被掀起来一角。吐尔逊从店里冲出来:“电闪了,别怵。”话音未落,巷口“嗡”的一声,半条街的灯暗了一瞬,旋即又亮了。
大家心里同时悬了一下,又同时落了地。李明对着屋里喊:“苏蔓,把冷柜那份抄一份放手机里,再打一份纸,放吐尔逊那边。”苏蔓“好”的声音很利落,转身就去做。小风小浪,没有把人心搅乱,大家的动作像磨合过的齿轮,咬得严实。
夜里,李明准备收工时,电话响了一下。母亲的号码。他接起来,母亲的语气一如往常,不快不慢:“你爸今天晚一点,工地那边下了小雨,他在那儿看着,别担心。”
她停顿了一下,又问,“你们那边风大不大?”李明说:“大,不过都稳着。”母亲“嗯”了一声,像是在点头,“你别夜里想着那些事,睡觉前把肩放下来。”
李明笑了笑:“我放。”挂了电话,他把那张“路与线”的小纸条翻出来看了一眼,心里那个“线”的头又握紧了一点——人不慌,路就不乱。
第三天一早,买买提江把车开到院里,车头冲着巷口。他打开后备箱,里头规规整整码着那批礼盒的外箱。
他拍拍箱角:“阿衣丁那边定下了,明天一早要用,今天晚上得先走一拨。”阿衣丁从墙根探出半个身子,脸上不自觉地挂着兴奋:“我爸妈一辈子都没见过这种‘整整齐齐’的礼盒。”
他说到这儿,又低了低头,“我怕出了岔子。”李明笑:“怕就对了。怕,会让人把事盯紧。”他看了看表,“今天不讲别的了,就帮你把这件事做好。”
院里活儿一下子集中起来。古丽把名单对了一遍,苏蔓把包里的那卷细绳拿出来,吐尔逊从店里拖出两块冰板放在门槛,嘴里叮嘱:“路上别晃,车别抖。”
买买提江把车子调了个头,让后备箱正对着过道。马合木提蹲在地上,手指摁着胶带,动作熟练又仔细。胡老板站在门口,不插手,只看——他这种看,像老匠人看年轻人做活,目光不苛,可一句话落在点上。
忙到夜里,最后一箱封好。阿衣丁抱着那张单子,手指在数字上停了一下,又挪开。他抬头,看见李明站在车后,嘴角抿着,一副不用他开口就知道他在想什么的样子。
阿衣丁走过去,小声说:“我知道,你怕我激动,怕我丢了东西。我也怕。这一车对我很重要。”李明点头:“对你重要,也对我们重要。你不只是把礼盒送去给亲戚看,更是把这段路走了一遍,走完以后你就知道以后怎么走。”
阿衣丁“嗯”了一声,眼睛有些亮。
车子出去时,巷口的灯白得安稳。买买提江探出手挥了一下,车灯照出一条光,像从巷口拉到街心的一根线。吐尔逊把门半掩着,背影贴在光边上。胡老板站在院口,忽然低声说了一句:“看得出门路的人,不会喊,你看他就行。”
没人接话,风轻轻从屋檐底下过去,像人松了一口气。
夜里散得晚。屋里只剩下三个人。苏蔓把“准备会”的卡纸收起来,压在厚本子底下,抬头说:“我跟我妈又聊了一会儿。她还是那意思,说‘女孩子家,别折腾’,我就把今天拍的东西发给她,她没回我,但我看见她点开了。”
她笑了一下,又揉了揉眼睛,“我不想她担心,但我也不想走。先这样吧。”古丽“嗯”了一声,没有劝,只把桌上的水杯推过去一点。李明把明天的那张便签写完,贴在文件夹里,不再多说。
第二天一大早,阿衣丁回来了。人还没进门,笑声先到:“到了,亲戚都说好看。”他把两张照片递过来,照片里,院里摆着一排礼盒,老人家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。
李明接过照片,看了很久没有说话。古丽在旁边看一眼,就知道他心里那根弦又被绷直了一截——不是因为赞美,而是因为“没出岔子”,这四个字对他们来说,分量比好听话还重。
这天午后,赵书记又来,肩上落了些风沙。他没寒暄,开门见山:“县里那边行程定了,后天上午,地点在县文化活动室。你们三个人去,讲完就回来,不安排饭局,不拉横幅,干干净净的。”
他把一张简单的安排表放桌上,“这回不光是镇里人,有周边两个乡的人也来。”他顿了顿,“你们不要想太多,讲你们的日常就行。记住——别讲自己有多了不起,就讲你们怎么把事说在前头、怎么把人留在身边。”
这段话落下,屋里没有人说“好”,也没有人说“没问题”。三个人同时点了一下头。那是他们对“下一程”的姿态——不抢先,也不退后。
傍晚时分,天边的云被风吹得像磨薄的纸。吐尔逊把电表又看了一眼,冲院里喊:“稳着呢。”胡老板带着他那壶奶茶过来,照例放在桌上:“喝一点,别老忙着。”
他坐下,忽然把声音压低了一点:“我听说,城里有人找了个不认识的年轻人,打算用你们的名头做‘团’。这事儿,不用去找他闹,你们把你们的唛头再明显一点,别让善意的人找错门。”
李明点头:“我们不追。我们把自己看住。”
夜里,风停在屋檐下。院门外的路灯亮了一盏又一盏。李明把“县里分享”的提纲收起来,放在书里。
他坐到门槛上,仰头看了一会儿天,没想那些新名词,也没想那些计划,只想起父亲说过的那句话——“路修好了,人心就不慌。”他心里头浮出另一个念头:路修好了,人心也要有人看着,不能只靠风。
他站起来,回屋,把明早要带的三样东西放进包里:一支用旧的黑笔,一张被折出白痕的流程卡,一张孩子写的“请把字写在格子里”的练习。
东西不多,但每一样都扎实。他把灯关了,门边那盏走廊灯亮在黄里透白的度上,像一口温着的水。
风真的停了。可李明知道,风随时会再起。巷口起风,人心要稳——他在心里轻轻说了一遍,像给自己也像给这一院子的人听。
然后他转身,睡觉。明天还有话要讲,人在场,话说清楚,路才会在脚下长出来。